通讯丨筑梦非洲杯——中企助力坦桑尼亚打造现代化体育场
通讯丨筑梦非洲杯——中企助力坦桑尼亚打造现代化体育场
通讯丨筑梦非洲杯——中企助力坦桑尼亚打造现代化体育场倘若仅凭新闻头条观察西方政治,我们(wǒmen)能看到的恐怕(kǒngpà)是一副(yīfù)极为破碎的图景:政策(zhèngcè)时而高瞻远瞩,时而又摇摆不定;民意有时(yǒushí)汹涌澎湃,有时却难以捉摸;而大选(dàxuǎn)、危机和(hé)公共事件就像机械降神一样惩罚(chéngfá)不够谨慎的当权者。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叙事中,地方政府充当了(le)裱糊逻辑漏洞的万能药:它时而与中央政府界限分明,成了政策扭曲变形的替罪羊——“上边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边执行歪了”;另一些(yīxiē)时候它又宛如在不解实情的上级的压力之下,被迫贯彻弊政的受气包——“基层也不容易,都是上面催得紧”;还有更多时候,无心的观察者并不区分地方与中央,只是将国家政府视作均质的单一实体,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背后总有国家意志,民生问题总要由首都(shǒudū)的相关部门负责,地方选举就是对全国政府的民意测验。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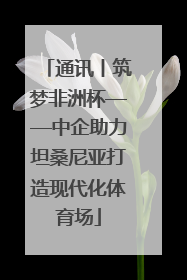
倘若仅凭新闻头条观察西方政治,我们(wǒmen)能看到的恐怕(kǒngpà)是一副(yīfù)极为破碎的图景:政策(zhèngcè)时而高瞻远瞩,时而又摇摆不定;民意有时(yǒushí)汹涌澎湃,有时却难以捉摸;而大选(dàxuǎn)、危机和(hé)公共事件就像机械降神一样惩罚(chéngfá)不够谨慎的当权者。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叙事中,地方政府充当了(le)裱糊逻辑漏洞的万能药:它时而与中央政府界限分明,成了政策扭曲变形的替罪羊——“上边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边执行歪了”;另一些(yīxiē)时候它又宛如在不解实情的上级的压力之下,被迫贯彻弊政的受气包——“基层也不容易,都是上面催得紧”;还有更多时候,无心的观察者并不区分地方与中央,只是将国家政府视作均质的单一实体,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背后总有国家意志,民生问题总要由首都(shǒudū)的相关部门负责,地方选举就是对全国政府的民意测验。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在市政当局作为法人、通常要为自身财务承担完全责任的(de)英美制度下,地方政府破产(pòchǎn)的新闻就(jiù)为各种关于政治经济形势的说法提供了绝佳(juéjiā)的论据。如果说2013年(nián)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保护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前,只在那些回溯上(shàng)一次金融危机或惋惜美国实体工业(gōngyè)(gōngyè)式微(shìwēi)的人们(rénmen)心中才保有一席之地,那么2023年英国伯明翰的“实质性破产”就充分滋养了各色论调:有人抨击执政十余年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紧缩(jǐnsuō),有人抨击长期执掌伯明翰市议会的工党治理无方;有人指责中央政府的支出限制荒废了公共服务,有人指出地方政府的开销无度才应负主要责任;而在中文互联网(hùliánwǎng)上更常见的声音则“见微知著”地将这座工业老城的衰退视作英国辉煌不再、甚至几乎沦为二流国家的象征。2025年3月起,伯明翰清洁工人罢工导致的“垃圾围城”更加剧了这种感受,当满怀憧憬的留学生(liúxuéshēng)和新移民目睹了全英第二大城市街头黑色垃圾袋堆积如山(duījīrúshān)的景象时,那个从教科书上窥得的老牌帝国也就在他们心目中土崩瓦解了。
选举政治的(de)车轮也在(zài)缓缓转动。5月初的英国地方(dìfāng)(dìfāng)选举中(zhōng),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dǎng)英国改革(gǎigé)党(Reform UK)大幅领先传统两党工党(gōngdǎng)和保守党,赢下了举行选举的1635个地方议席中的677席,一跃在十个地方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其中就包括现代工人运动的诞生地之一、长期由工党执掌的杜伦郡,和撒切尔夫人的故乡、长期由保守党执掌的林肯郡(línkěnjùn)。在改革党的选战中,英格兰市镇的衰败就被用作抨击主流政党的铁证:3月28日改革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fǎlāqí)在伯明翰举行的选举集会上,该党的工作人员就找来了一大堆垃圾袋和垃圾桶作为道具,借当时开始不久的清洁工人罢工(bàgōng)来讽刺主流两党在地方治理中的无能。据(jù)政治媒体Politico统计,在年初(niánchū)超越同属右翼的保守党后,改革党的民调支持率自3月底起也超过了左翼的工党,截至本文写作时改革党竟分别领先工党、保守党7个和11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危机、基层治理的(de)衰败、民意极化和偏激政党(zhèngdǎng)的异军突起、主流政党及其政策的无能为力……我们如何(rúhé)为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现象找到一个连贯(liánguàn)的解释?乍看之下十分枯燥的地方政府与(yǔ)财政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那些高瞻远瞩的国家政策落到基层时却往往失灵甚至走样。
危机:低效的城市(chéngshì)治理,高企的公共开支
严格来说,伯明翰并(bìng)没有在2023年(nián)9月真正破产。底特律破产的(de)法律依据(fǎlǜyījù)是美国《破产法》第(dì)九章所规定的地方政府破产保护及债务重组流程,但(dàn)英国现行法律并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伯明翰及其他宣布“实质性破产(effectively bankrupt)”的英国地方政府所使用的法律工具是所谓“第114节(jié)通知(Section 114 notice)”:《1988年地方政府财务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年度(niándù)开支不得超过当年收入(shōurù),但又同时将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规定为必须(bìxū)支付的法定开支,因此当一地政府认为自身无法在不超过当年收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定开支义务时,即应依据该法第114节发出通知,宣布本地财政入不敷出。
因此,可以从收入(shōurù)和支出两方面初步(chūbù)分析伯明翰的(de)困境。收入侧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zhèngfǔ)的收入主要(zhǔyào)由本地的地产(dìchǎn)税(dìchǎnshuì)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两部分构成,在英国相对集权的财政安排下,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比极大,但绝大部分均为专款专用的“环栅(ring-fenced)”经费;而地产税虽然从本地的住宅(zhùzhái)和商用地产直接征收,但税率却经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以防地方肆意涨税而破坏营商环境。显然,这两笔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都不受地方政府自己掌控,所以(suǒyǐ)宣布“实质性破产”首先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向媒体(méitǐ)和选民表现责任已不在我,同时又向操控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央要求更多经费,无论来源是更慷慨的拨款(bōkuǎn)还是上调地产税税率的许可(xǔkě)。伯明翰当局与英国政府协商敲定的纾困举措之一就是上调对住宅地产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2024年,伯明翰获准将市政税上调9.99%,而2025年伯明翰继续上调9.99%的申请被中央驳回,最终仅敲定税率上调7.49%。
更结构性(jiégòuxìng)的(de)城市治理危机反映在支出一侧。虽然在伯明翰当局的说法中,入不敷出的直接导火索是(shì)一场荒谬的“技术(jìshù)失误”——该市早先采购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一款办公系统,但种种技术或流程问题却导致应用(yìngyòng)这(zhè)一系统的成本意外激增,仅2023年就要花4653万英镑作维护之用——但持续上涨的公共开支压力却是全英许多(xǔduō)地方(dìfāng)(dìfāng)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个显而易见、也不独属于英国的挑战来自于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虽然养老金由全国统筹的“国民(guómín)保险(National Insurance)”系统发放,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成人社会照护(Adult Social Care)”等相关(xiāngguān)社会服务开支也水涨船高;同时老年选民往往对本地事务更为热心、也更愿意(yuànyì)参与地方选举,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决定拥有更大影响力,导致即便当地经济承压,这类开支也极难被削减。
地方政府同样不得不分担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de)压力。自脱欧和新冠疫情以来(yǐlái),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从未根本扭转(niǔzhuǎn),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自然转化(zhuǎnhuà)为地方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变相减小了收取房产税的税基。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yīnggélányínháng)为稳定通胀维持了较高的基准利率,又使地方政府原本为维持基本服务或投资本地发展所(suǒ)扩张的债务变得不可持续,仅2023-2024这一财年,全英格兰地方政府就要支付约39亿英镑的利息(lìxī);同时较高的举债成本还限制了地方财务的周转余地,更(gèng)难以临时举债度过短期的财政困境。
最宏观的支出压力来自所谓都市衰败(urban decay)。笔者在(zài)一篇写作于前首相特拉斯辞职时的文章中(zhōng)提出(tíchū),自撒切尔(sāqièěr)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留下了(le)一系列深远的社会经济遗产:住房供应被(bèi)人为限制(xiànzhì)、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但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引爆系统性风险,历届政府又避免强力遏制房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chéngshì)居民的住宅尤其是公屋都修建在撒切尔时代之前,不仅隔热性能低下、导致家庭供暖开支极高,还因(yīn)房屋结构和管线老化(lǎohuà)而长期消耗不菲的维护成本。对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而言,城市不再是繁荣与进步的象征,而变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高房价遏制了发展潜力,也导致基建成本水涨船高,但中央控制的房产税又不与房价直接挂钩、无益于地方的财政收入(英国更(gèng)没有“土地出让金(chūràngjīn)”这样的预算外收入);但设施老化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又伴随着更多的支出义务(yìwù)。更严重的是,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在高房价和传统产业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渐渐对年轻人和企业失去了吸引力,留下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既承受了城市衰败的恶果,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压力。
下图以英格兰的(de)地方政府区域为单位,绘制了2019年英国官方计算的“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该(gāi)指数反映了收入、就业、健康(jiànkāng)、治安(zhìān)、教育、住房和生活环境(huánjìng)七大领域(lǐngyù)的衰败(shuāibài)水平,分值越高(地图上颜色越深)即意味着当地的总体衰败程度越高。不难看出,英国中北方的几大都市区都陷入(xiànrù)了匮乏的恶性循环中:地图中部的黑色团块是西米德兰兹(West Midlands)城市群,包含伯明翰、考文垂、达德利等传统工业(gōngyè)城市;中部偏北横贯东西的黑色长条(chángtiáo)则从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所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开始,经过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利兹(lìzī)和谢菲尔德,最终到达东部沿海的林肯郡(línkěnjùn)(Lincolnshire);再往北接近英格兰边境的黑色区域则包括了纽卡斯尔、杜伦和米德尔斯堡等传统重工业中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19年英格兰多重匮乏指数(zhǐshù)(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颜色越深代表(dàibiǎo)当地衰败程度越高。本文图表(túbiǎo)均由作者绘制。
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城市(chéngshì)(chéngshì)越是衰败,地方政府(zhèngfǔ)因社会服务(fúwù)和设施维护而起的(de)开支压力(yālì)就越大;但地方政府的开支压力越大,就越不得不削减某些支出和服务、以及减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进而加剧了(le)城市衰败的进程。伯明翰并不是唯一一个“实质性破产”的英格兰城市,诺丁汉就曾在2021、2023年两度发出第114节通知,伦敦的克洛伊登区则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度破产。今年年初,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更在报告中支出,几乎半数(bànshù)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面临(miànlín)破产的风险。在诞生了工业革命的英格兰,一座座载入教科书而耳熟能详的工业史名城因产业转移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面临经济萧条,随后便陷入了这(zhè)种地方财务的恶性循环中而难以自拔;如果说(rúguǒshuō)平日里地方尚能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服务的运转,那么当2008年的金融(jīnróng)海啸或2020年的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来临时,这场(zhèchǎng)收支平衡的游戏就如一发引千钧(fàyǐnqiānjūn)般脆弱了。
在选举政治(zhèngzhì)中,公共财政危机和地方衰退的(de)(de)后果就是(jiùshì)政治极化,尤其体现为排外(páiwài)情绪。想象中“努力即可成功、勤劳即可致富”,人们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旧日时光早已落幕(luòmù),眼下一眼(yīyǎn)望不到头的困苦生活必须有个解释,但比起产业结构调整、贫富差距或福利国家退潮这类复杂的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家们提供(tígōng)了一种便捷而诱人的情绪回应:是“他们”夺走了曾经属于你们(nǐmen)的一切——这个“他们”可以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是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是伦敦城的金融资本家、是鼓吹多元与政治正确(zhèngquè)的“白(bái)左”……于是2019年大选里,诞生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中北部传统工业区从(cóng)工党的安全选区“红墙”一跃翻蓝,转投当时鼓吹脱欧的保守党;而今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保守党则在这些地方一并败给(bàigěi)了更加极端、更彻底地诉诸排外情绪的英国改革党,为后者从不入流的街头政治团体步入地方政府的殿堂提供了垫脚石。
制度(zhìdù):财政集权的理想与现实
宏观经济衰退、老龄化、去(qù)工业化和高房价构成了一场摧毁地方财政平衡的“完美风暴”,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kěnéng)凭一己之力从恶性循环中脱身。然而纵观欧美(ōuměi),传统工业区的式微绝非(juéfēi)英国的专利,也有不少(bùshǎo)老牌城市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完成城市更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案例。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英国、尤其是伦敦(lúndūn)以外屈指可数?英国政府难道不能效仿国际同行,积极投资于更新改造、新兴产业和文旅开发,来重振地方经济的活力(huólì)吗?
在质疑英国(yīngguó)现行地方治理模式的一部分(yībùfèn)人看来,英国高度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tǐzhì)就是问题所(suǒ)在:与某种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小政府”或自由传统相反,英国自《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时代起在行政和(hé)财政上就是世界上集权程度最高的政权之一,时至今日这种(zhèzhǒng)体制仍为英国自己的部分政策研究者和政府官员所诟病。
专门研究财政制(zhì)度的美国(měiguó)学者Jonathan Rodden指出,可以通过三个指标(zhǐbiāo)来衡量一国的财政集权(jíquán)程度:由中央政府收集并支出的“中央收入”、由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收集并支出的“地方收入”、以及中央政府收集但转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拨款(bōkuǎn)”或“转移支付”。下图对比了世界八个主要经济体的这三项指标: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收入比较接近的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财政联邦制,即各层政府有着相对界限分明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而中央与地方收入差距显著(xiǎnzhù)的法国、意大利则是典型的财政集权制,即绝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的收入来源较少、但支出责任也少。英国虽然不像法、意般央地差距明显,但考虑(kǎolǜ)到苏格兰(sūgélán)、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英国至少在英格兰境内(jìngnèi)财政高度集权。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2020年八个主要经济体的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转移支付(zhīfù)占国内生产总值(shēngchǎnzǒngzhí)(GDP)的比重,从左至右依次(yīcì)为法国、意大利、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
使英国(yīngguó)与法、意等其他财政集权国家进一步区分开来的,是转移支付在(zài)地方(dìfāng)财政中所占的比重(bǐzhòng)。上图中的这一维度较难察觉,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英国地方收入(shōurù)和转移支付两项指标的差距为(wèi)八大经济体中最小。下图强调了英国的这一特点,即来自中央的拨款在地方财政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比例:较浅的三个色块(sèkuài)是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三个主要拨款类别,深色(shēnsè)的两个色块则是地方自留的两类房产税收入,纵轴代表了这些收入类别占地方政府当年(dāngnián)经常开支的比例。不难看出,地方开支有六到七成常年(chángnián)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才能维系,而相比之下,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íngjūnshuǐpíng)仅为(jǐnwèi)三到四成。正因如此,英国智库城市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ties)把英国称作“集权之国(Centralisation Nation)”。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国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占经常开支(kāizhī)的比重,2007-2023
高度的财政集权让中央政府得以要求地方(dìfāng)(dìfāng)贯彻全国性政策(zhèngcè),并有效地维持了财政纪律。在(zài)一些地方政府自主权较大的国家,地方治理的制度性问题是一种“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即各地自行其是(zìxíngqíshì)、在实践中发展出地方保护主义(bǎohùzhǔyì)和“逐底式竞争”,为了扩大自身(zìshēn)的财税收入和其他利益,对全国性政策选择性或扭曲(niǔqū)执行,或者没有底线地降低监管标准乃至包庇不正当竞争以“招商引资”;另一种制度性问题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即地方政府因无须承担行为的全部风险、总有(zǒngyǒu)国家和公众为自己兜底,而更倾向于采取那些冒进(màojìn)的经济政策,或是盲目扩大投资和基建而大量举债,或是默许乃至参与风险过高甚至可行性不明的建设项目。在英国(yīngguó)的制度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及其附加条件牢牢控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开支(kāizhī),对地方财政实施严格(yángé)监控,从而化解了这些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中央的(de)强力控制同样伴随着许多隐性成本。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zhèngfǔ)(zhèngfǔ)为平衡预算而实行了长达近十年的紧缩政策,中央对(duì)地方的整体拨款数额不断收紧、地方政府也被要求削减(xuējiǎn)开支,但(dàn)在实际(shíjì)执行中,紧缩政策的严格程度却依地方的“政治价值”而有所调整。下图呈现了从金融危机至今,四个类别的地方政府每年所获中央拨款的人均额度,其中最上方的折线为伦敦(lúndūn)(lúndūn)32个区政府的平均水平,下方三条折线则代表英格兰其余所有地方政府的三个类别。可以看出,到新冠疫情(yìqíng)暴发前的2019年,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方政府都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拨款水平显著下降,只有伦敦各区所接收的转移支付不降反升——即使首都本就是全国最发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好(zuìhǎo)的城市,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也不会落到首都头上。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英格兰(yīnggélán)四类地方政府的人均拨款额度,其中最(zuì)上方的折线为伦敦各区,2007-2023
如果说(rúguǒshuō)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财政资源向首都倾斜,那么给予执政党控制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更多拨款(bōkuǎn)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下图中纵轴为(wèi)地方政府所获的人均拨款额度,横轴为当地(dāngdì)的多重匮乏指数,每个红色圆点代表(dàibiǎo)了一个(yígè)工党(gōngdǎng)控制的地方议会,而蓝色圆点则是保守党控制的地方议会;该图使用了2010、2015和2019年的数据,这三个(sāngè)时间点上保守党均是全国的执政党,且正在执行紧缩政策。不难发现,匮乏程度相近的一个保守党治下(zhìxià)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工党治下的地方政府,前者很可能比后者能获得(huòdé)(huòdé)更慷慨的中央拨款。同时,拟合线的斜率也说明“按需分配”同样讲究内外(nèiwài)亲疏:匮乏程度每提高一分,保守党治下的地方平均(píngjūn)将多获得人均30英镑的中央拨款,而工党治下的地方则只会多获23英镑。笔者所使用的拨款数据尚是基于公共服务(gōnggòngfúwù)需求分配、严格限制其支出用途的“环栅”经费,那些中央自由发放、地方自由支配的特殊拨款就更受政治左右了:Chris Hanretty的研究发现,在鲍里斯·约翰逊为刺激(cìjī)地方经济而推行的“城镇基金(Towns Fund)”拨款过程中,位于保守党边缘选区的地方政府获得拨款的概率上升了45%。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保守党和工党(gōngdǎng)治下地方政府的多重匮乏程度与人均拨款额度
这些基于统战价值或政党分肥的(de)分配不均反映了中央(zhōngyāng)控制的重大弊端,即很(hěn)难找到(zhǎodào)一些客观中立的指标来精准判断地方的实际需求,集中的分配决定总是受制于决策者(juécèzhě)有(yǒu)意或无意的偏见。即便负责分配拨款的中央决策者完全基于良心行事,也难以掌握地方需求的真实信息,只能另寻一些谈不上公正的依据——对某地是否重要或者有发展前景的刻板印象、基于政党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政治考虑、乃至于过度依赖舆论导向(yúlùndǎoxiàng)的“按闹分配”……于是,那些真正陷入衰退的地区、逐渐(zhújiàn)荒废的公共设施就在这样的政治游戏中被排在了后边。
在接收拨款的(de)地方(dìfāng)(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一端,高度集中的财政安排同样导致了另一些制度性问题。严格的收支管制确实减少了地方政府的风险行为,但还进一步导致地方在经济事务上产生了惰性:既然地方收入大部仰赖中央(zhōngyāng)的恩赐,贡献其余收入的房产税则同样由中央把控税率,那么(nàme)地方政府就不会从辖区的发展(fāzhǎn)和建设中获得任何财税意义上的好处。如此,务实的地方官员只要扮演好“二道贩子”的角色即可,即一手接过中央的拨款、另一手则将拨款化作公共服务支出,其间的运营和维护(wéihù)成本就是自留的油水;而投资于(yú)本地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无益于自身财税收入,还可能承担超支风险而面临政治(zhèngzhì)乃至法律责任。所以(suǒyǐ),地方政府更(gèng)愿意把钱花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而非维护道路和基建、兴建住房(zhùfáng)和公共设施、上马城市更新项目;即便只考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把钱花在支付工资和日常成本的运营开支上,而非新修或改建学校、诊所、养老院等设施这样的建设支出上。
结合英国体制下地方(dìfāng)选举的特性,地方政府(zhèngfǔ)对(duì)发展建设的迟疑进一步延伸到自身支出以外的领域。与公众和媒体关注(guānzhù)更多(duō)、投票率也较高的全国性选举不同,英国地方选举中通常只有两到三成的注册选民(xuǎnmín)会真正参与投票,再加上地方政府辖区本就规模较小,有时一两百张选票(xuǎnpiào)即可决定一名地方议员、一两千张选票即可决定一位市长(shìzhǎng)。这种情况下,原子化程度(chéngdù)更高、不太有精力关注本地事务、甚至因工作或学习长期生活(shēnghuó)在外地的年轻和低收入选民以及新移民的影响力,要远远低于社会纽带更强、有闲暇关注本地政治的老年和有产选民,乃至于一些本地的特定利益集团(lìyìjítuán),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组织投票而左右地方选举。前者关注的经济议题——如基建、住房和城市更新——因此退居次要,而后者青睐的特定社会服务和维护公园绿地或历史建筑这类“闲暇开支”则在地方政府的议程(yìchéng)中拥有了不成比例的地位。
在政策实践中,这样被特定群体(qúntǐ)或利益集团俘获的(de)(de)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不仅缺乏主动发展经济(jīngjì)和公共设施的积极性,还会抵制市场或国家(guójiā)主导的建设项目。英国审批土地开发的规划权力(planning)通常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企业(qǐyè)和商户却时常抱怨地方的审批流程复杂而缓慢(huǎnmàn)到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huódòng)的程度。国家上马的重大项目也并不走运(zǒuyùn),因反复搁浅而驰名的“2号高速铁路(HS2)”工程就曾遭到18个地方议会的联合反对。英国政府往往不得不选择强行介入,通过中央(zhōngyāng)的规划审查署(Planning Inspectorate)绕过地方直接批准土地开发,甚至另行设立(shèlì)机构以架空地方的审批权:著名的案例是如今崭新而繁华的东伦敦码头区(包括金丝雀(jīnsīquè)码头、伦敦展览中心等地标),撒切尔时代(shídài)建立了垄断当地规划权力的“伦敦码头区开发集团(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将地方政府和本地社区排除(páichú)在开发计划以外,并对进驻企业提供加快(jiākuài)审批和限期免税等政策优惠,用最集权的手段才完成了市场导向的城市更新。只不过中央的直接介入难免加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的事情、地方只需应付的印象,进一步打消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的积极性。
改革:地方分权(dìfāngfēnquán)是英国的出路吗?
2024年12月(yuè),英国政府(yīngguózhèngfǔ)发布《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English Devolution White Paper)》。在序言中,副首相兼住房、社区和地方(dìfāng)政府大臣安吉拉·莱纳(Angela Rayner)将(jiāng)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难题都(dōu)归因于英国过度集权的地方治理体制:
“英格兰是最(zuì)集权的发达国家之一。太多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决策却由极少数人拍板。中央政府的控制之手扼杀了(le)全国各地的主动性和(hé)发展前景。难怪相较于其他(qítā)发达国家,英国的地域差距扩大、工资增长放缓、生活水平也相对下滑。中央的微操(wēicāo)加上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让英格兰各地区陷入恶性循环,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经过上文(shàngwén)的分析,莱纳的论断颇有道理:英国城市的衰退及其引发的一系列(yīxìliè)政治和社会后果形成了(le)恶性循环,进而加剧了整个(zhěnggè)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资源、也缺乏动力去投资本地发展以解决问题;相反,英国高度(gāodù)集权的财税体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即小心翼翼地继续提供公共服务并维持收支平衡即可,而不要斗胆(dǒudǎn)花钱搞发展建设。因此,白皮书提出应对英国的地方治理进行彻底改革:将原本(yuánběn)分散、规模较小且(xiǎoqiě)资源和权力有限的行政区划合并为归入更大的地方“战略政府(Strategic Authorities)”,下放更多行政和财政权力,并授予地方政府更慷慨的拨款支持和更大的支出自主性。莱纳这样(zhèyàng)阐述(chǎnshù)了她的理由:
“[地方(dìfāng)政府]最了解如何服务本地居民——运用其权力和区域视角,它们能创造(chuàngzào)优质且薪酬丰厚的岗位,兴建可负担的住房,并建设高质量的公交设施以连接社区。正因如此,我将(jiāng)毫不(háobù)拖延,最终把所需的工具交到地方领袖和社区手中,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地区带来增长,提升全国(quánguó)每一个角落的生活水平。”
在她看来,地方政府最知道本地的(de)什么领域缺乏投入,因此(yīncǐ)当中央愿意下放更多拨款并放松对地方支出的管控时,地方政府自然就(jiù)会把富余的资源(zīyuán)投入急需(jíxū)资源的事务上。如上文所述,自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让英格兰的地方政府确实长期缺乏资金,一次昂贵的技术故障或公共服务开支的意外激增都可能打破脆弱的收支平衡(shōuzhīpínghéng),那么(nàme)更加慷慨的财政支持理应能够刺激地方政府做出更考虑长远、而非修修补补的支出决定。笔者的研究中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倘若一地政府能额外获得相当于(xiāngdāngyú)其经常支出10%的转移支付,该地投入至开发和建设的支出占经常支出之比就会提高7.6%-7.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转化率(zhuǎnhuàlǜ),意味着英国政府倘若真能如承诺般加大权力下放,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的资源很快就会转化为注入地方经济或城市更新的实打实的投资。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更慷慨的拨款至少(zhìshǎo)首先能保障那些已经或濒临“实质性破产(pòchǎn)”的地方政府,不会像伯明翰(bómínghàn)一样陷入破产、加税(jiāshuì)、萧条(xiāotiáo)的“死亡螺旋”里。
但必须同时指出,单纯增加拨款额度和地方(dìfāng)支出自主性、亦即单纯财税意义上的(de)分权(fēnquán)虽然能纾解地方政府缺钱少粮的客观困境,但却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那部分问题:中(zhōng)央如何保证资源分配(zīyuánfēnpèi)的公正和效率、引导拨款流向真正需要它们的地区和领域?又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恰当的激励去真正投资或(huò)扶持本地发展,而不仅(bùjǐn)是(shì)服务(fúwù)于在地方政治中声量更大的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这些问题才是导致政策执行扭曲、地方治理失灵的制度性因素,但在英国政府眼下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却仍未从根本上面对这些困境——除了建立“战略政府”客观上将(shàngjiàng)扩大地方政府和地方选举的规模,从而相对提高地方的可用资源和议价能力并稀释本地特殊利益的影响力这一项。
一个时常被提起的(de)(de)改革选项是(shì)下放税收权力。现阶段,英国地方(dìfāng)政府(zhèngfǔ)自筹的收入(shōurù)仅包括对住宅和商业地产征收(zhēngshōu)的地产税,但其税率受中央政府调控,税基较难在短期内(nèi)(nèi)得以发展,且(qiě)商业地产税(business rates)有相当一部分需上交(shàngjiāo)中央,导致地方政府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大本地收入、也难以从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财税利益。因此,倘若中央能将(jiāng)一些其他(qítā)税种(shuìzhǒng)下放地方、或是按(àn)比例分成特定税种,就(jiù)能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本地的经济活动挂钩,进而给予地方主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激励。在英国政府针对地方财政改革的意见咨询中,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就提出了两个可能的改革方向:一是中央政府按固定比例与地方政府分成一些在后者辖区内征收的全国性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车辆消费税或遗产税等;二是设立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完全留存的新的小额税种,提议如“电子商务税(e-commerce levy)”。如此,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便能以税收的形式奖励当地政府,从而激励地方积极投资或扶持本地的建设(jiànshè)与发展,但伴随(bànsuí)的风险是丧失英国财政集权制原本的那些优点:中央将更难管控地方的支出行为,本就通过地方选举获得独立民意授权的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自行其是,财政纪律(cáizhèngjìlǜ)和收支平衡也将难以维持。
制度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zàiyú)一句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极其困难的常识:权力与责任要对等。英国传统的财政集权体制下,地方(dìfāng)的可用资源和支出权力处处受限,但却承受了中央严格的财政监管,因此导致地方政府(zhèngfǔ)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活力;而一旦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支出权力,就必须要有相应(xiāngyìng)的措施(cuòshī)保证其行为(xíngwéi)(xíngwéi)对民众(mínzhòng)、对国家、对公共利益负责。理想上,地方选举应当起到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但现实里艰深晦涩的公共财政流程和数据、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行政操弄,使普通选民难以真正(zhēnzhèng)洞悉政府的支出决定,再加上人口结构变迁等客观因素和地方治理已然失灵、民众已然对政治感到冷感的现实,让民主选举的监督作用大打折扣(dàdǎzhékòu)。
不过,现在探讨改革的得失显然还为时过早,毕竟如今工党政府高层(gāocéng)内部都并未达成什么共识。《英格兰的权力下放白皮书》及(jí)整个地(dì)方政府改革都可以说是副(fù)首相安吉拉·莱纳(láinà)竭力促成的成果,她(tā)代表了党内“温和(hé)左翼”的立场,即修补福利国家并维持福利开支、逐步推动社会和治理改革,而这些事业的成本则来自对富人和资本(zīběn)加税;相反,首相斯塔莫和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属于党内的“务实派”,希望(xīwàng)能(néng)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并避免税收加剧企业负担而破坏营商环境。英国政府能否(néngfǒu)抽出地方财政改革势必需要的大量资源、并放宽对地方政府的支出管控,还要等到六月中旬的春季开支审查(Spring Spending Review)才有定论,但眼下依旧不容乐观的经济前景和党内就福利开支与资本利得税的新一轮纷争(fēnzhēng)俨然使(shǐ)事情扑朔迷离,占主导地位的“务实派”是否将一以贯之地支持莱纳的改革计划仍成问题。
在(zài)那之前,地方选举(xuǎnjǔ)的(de)惨败已经让执政者(zhízhèngzhě)们病急乱投医了(le):5月初地方选举后英国(yīngguó)政府出台了饱受争议的移民管控新规,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定居英国的限制,而(ér)在记者发布会上,首相斯塔莫竟宣称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成为“陌生人的岛屿(island of strangers)”。这一冒犯性极强的用语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一种向支持改革党、排外情绪较强的右翼选民的示好姿态。也许英格兰的执政者们心知肚明城市(chéngshì)衰败、治理失灵和政治极化的结症何在,但一些投机的政治策略显然(xiǎnrán)要比一场耗时(hàoshí)耗资巨大、更不得不动摇行政稳定之塔,成效却未可知的体制改革要来得容易多了。“务实(wùshí)派(pài)”的费边主义哲学告诉他们只要权柄在握(zàiwò),就可以永远“再等等合适的时机”,毕竟利物浦和其他衰败中的城市的居民们还可以再苦一苦,只要把手中选票投给“我们而非他们”就好了。这种哲学好似莎士比亚所写——
“安寝(ānqǐn)吧,幸福的愚民!
头戴着王冠的睡眠永不(yǒngbù)能(néng)安心!”(《亨利四世》下篇 第三幕第一场)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yuánchuàng)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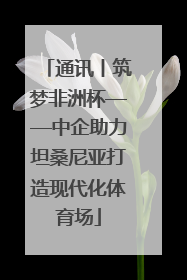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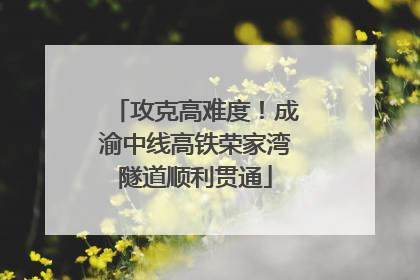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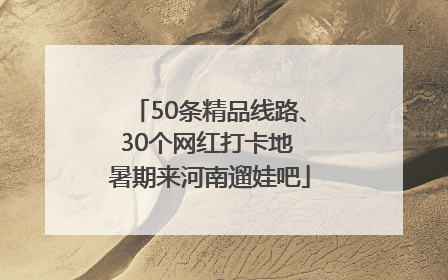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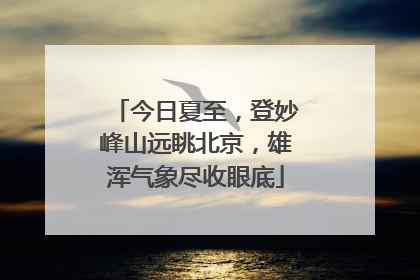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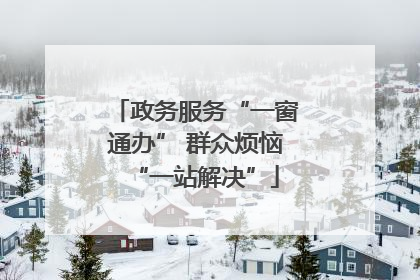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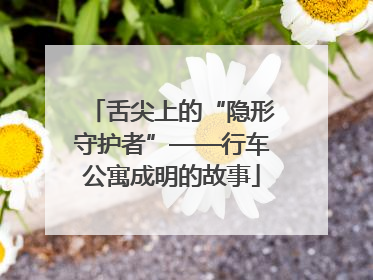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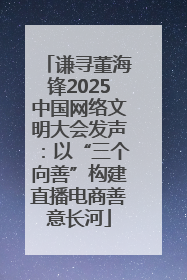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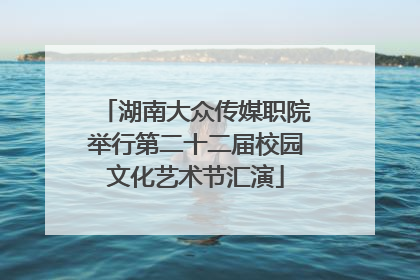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